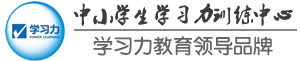三、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的文学艺术
(甲)汉字密码与欧洲的中国化
最近十多年,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尤其是它的中国观,备受冲击而摇摇欲坠。让我们来介绍与此相关的大卫·波特教授所写的两部书。
第一部书是《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其大致内容为:
从1583年第一次成功赴华的耶稣会士到1816年英国贸易使华团的失败,在这两百余年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实践魔幻般地吸引了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以及社会批评家。
其直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极深刻的:从欧洲宫殿花园的中国茶馆到大众舞台改编的中国戏剧,从呼吁按照中国的科举文治模式创立西方政府体制、到尝试儒家式的儿童道德教育。然而,比显而易见的模仿和引进更重要的则是“解读策略”,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中,欧洲人通过翻译和编译,把那闻所未闻、玄之又玄的中国的典籍典宪,想方设法变成了他们熟悉的语义形式;由此,让它们汇成新兴的欧洲现代话语。……该书还追溯了欧洲通过“想象中国”,进行自我构建的文化创举,主要是在四个凸出领域——语言、神学、美学和经济。
大卫·波特的另一部书是《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它的大致内容为:
18世纪的英国日益被卷入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并且复制后者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英国的消费者迷恋异域情调的东西,也就是中国风格的商品、艺术和装饰物。然而,他们也经常被这些商品中所体现的外来审美,给搅乱了。……大卫·波特分析了这一过程,即中国美学思想是如何被英国所同化的。
虽然对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个案研究,看上去很反常——两人分享“中国风”,却又仇视之;但是,大卫·波特做了充分的诠释,那就是在18世纪,“中国风”的奢侈、消费、品味和美学观念都逐渐转向(英国)民族主义。他例举了许多中国和中国灵感的物品与艺术,它们构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史的主要方面。
柯林斯博士说:
【“18世纪的英国复制中国商品和消费文化皆有助于形成不列颠自身的现代性。”】
大卫·波特还进一步论证:现代早期欧洲的进步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而欧洲在知识和文艺方面的成就则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明朝和清朝早期的瓷器(并且最终,英国人从中造出了仿制品)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大受欢迎。在1690年代玛丽女王引领这场热潮在她汉普敦王宫里摆满了蓝白色的花瓶和盘子,精英和中产阶级妇女纷纷效仿。在18世纪中期,没有壁炉架上不是摆着一个中国坛子,一个笑佛的。
大卫·波特提醒说,一件明朝瓷器,可以同时满足对古玩的渴望和对新奇物件的渴望。的确,在英国人眼里,蓝白色的瓷器是新奇的,但它又是“带有四千年血统之久的新奇物件”。因此这种“中国古玩热”开始影响到英国人的口味和英国家庭空间。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乙)“汉字表意”的西方写作
哲学家德里达这三句话耐人寻味:“文本以外无一物”、“对宏大叙事存疑”和“权力就是知识”。这个“权力”,我们理解为征服世界的“海权”;归根结底,它产生于西方幸遇的“天时地利”——由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科技西传等因素,把亚欧大陆西端的“海隅”的地缘政治提升了起来。
下面借喻德里达的话来甄审西方文学:
西方在其有了权力之后便伪造其知识传统与文化历史,包括《荷马史诗》这样的“宏大叙事”。《荷马史诗》有真实文本吗?常言,虽然荷马本人是眼盲加文盲,但它的口传故事则被后人记载下来,保存至今。可能吗?
——所以说“对宏大叙事存疑”。
再说,我们知道,表意文字(汉字)相对稳定,因而可以传播和传承;而“表音文字”则相反:在印刷术之前,“表音”是不可能的——随时随地都会变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会真实文本呢!既然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字和文学,那就是一无所有。
——所以说“文本以外无一物”。
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印刷和纸张才算有了文字,却是“各表其音、各执歧见”;没有合理合法的“表意”作为标准,争讼和冲突在所难免(宗教战争与此有关)。即使写下文本,那也是“辞不达义、词不逮意”,尤其是缺乏文学性和哲理性(例如所谓的“文艺复兴手稿”和旧版荷马、莎士比亚等)。
直到1700年左右,由于其表音文字有幸寄生于汉语内涵(表意、雅言),它才开始胜任于书写“古典、经典”;因此,那具有审美或文学价值的《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等,都是在18世纪这个“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及其所牵引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环境下,粉装玉琢、粉墨登场。
德里达还说:“汉语写作概念作为一种‘欧洲幻觉’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西学”——尤其是“古典西学”——是由汉语概念所形成的“欧洲幻觉”。
17世纪的欧洲精英们探索具有合理表意的通用语言,也称为“哲学语言”——“培根、霍布斯和威尔金斯皆相信,越是完美的语言越是包括着达到完美哲学的模式和方法。”换句话说,通过“完美语言”来建立学术(包括文学、科学和哲学),而“完美语言”(通用语言或哲学语言)则是基于合理表意的。毋庸置疑,这就是汉语特质。所以德里达提醒我们:莱布尼茨把汉字当做建立西方哲学的基石。
比奇洛教授解释道:
【他( 莱布尼茨)提出,中国书面语言是哲学语言的典范。换言之, 莱布尼茨想象有这么一种书写文字,它与思想形式本身直接挂钩,而非通过口语和具体物质来表达。……然而, 莱布尼茨这个梦威胁着这一成说,即欧洲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真理。……的确, 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是把数学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被 白晋说服,而把汉语当作完美模式,因为汉字起源于远古的易经象数。】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莱布尼茨时代,即在17、18世纪之交,所谓的“文艺复兴”及其所发现的“古希腊”都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两者都是在19世纪被“经典化”的(“文艺复兴”是1840年被命名和定性的,而“古希腊”则是更迟才成型的)。
反过来想:如果在17、18世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也具有如今的“历史意义”,那就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
第一,培根、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都把汉字当做“真正的字”,把汉语当做通用语言及哲学语言的典范;
第二,直接受中国影响而发生了塑造现代西方的三件事:中国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
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意象派文学运动等欧美世俗化进程的重大事件中,中国元素都是主要的催化剂,尤其是汉字的启迪,欧洲在智识生活上一直遭受的煎熬、困扰和瓦解才得以解脱。
(丙)汉字表意的西方文艺
汉语作为一种哲学或哲理的语言,深刻影响了西方诗学。罗伯特·克恩教授指出:
【根据(法国哲学家) 德里达,在17世纪,汉语书面语言“作为一种欧洲幻觉”在起作用;…… 莱布尼茨的相关思想,是希望借助于汉语来发明一种适合的哲学语言,使之成为哲学的工具……。 莱布尼茨和诗人 庞德所看到的是,汉语是人们所寻找理想的言语表达形式的楷模。
对于 费诺罗萨来说,汉语是美德和特权;毕竟,把它放在 爱默生的术语里,汉语则是意象和修辞的语言,由此不断提醒我们那是诗的起源……。 艾兹拉·庞德习惯地把汉字表意融入他的字母文字写作之中。】
“汉字表意”奠基了从诗歌到电影的西方或现代文艺,它构成了西方传统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兰·格林写道:
【在1977年, 阿洛多·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 1929-2003)汇编了一部著作,题为《表意文字:逻辑、诗歌和语言》(Ideogram: Logic, Poetry, Language),其特点是翻译被热议的 费诺洛萨的论文《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它是在 费诺洛萨去世后,由 庞德编辑出版的。该书还包括另一篇论,即 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于1929年写的《电影原理与表意文字》……。
正如 阿洛多·坎波斯所昭示的, 费诺洛萨是这一学统的哲学家和诗人之中的一员,即从 笛卡尔和 莱布尼茨到 爱默生和 庞德;他们寻求功能性的诗学框架,它是基于像表意文字的通用符号。】
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1853-1908),明治18年在日本三井寺法明院受戒皈依佛教,受戒名是“玄智院明彻缔信居士”。
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费诺罗萨通过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最富于诗性的语言。
费诺罗萨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中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的烘托。汉语重在“意”,学习汉语重在进行体验感悟,所以汉语具有突出的诗性。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及物性”,从来没有失去表现事物复杂功能及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它由象形的图案组合而成,不用符号。因此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能够达到事物本身。而且这种字体构造方式后先相续,基本精神从未中断,所以至今仍然“葆有原始的活气”,这也决定了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费氏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逻辑”是一种暴政,它使英语不再具有表现物象的能力,而变成任意专断的符号。西方语言讲究“词性”、“语法”,语言经过层层抽象概括,就使词语失去了字词直接表达“自然”的清新品质。词语被装进“词性”和“语法”的匣子,是违反自然的主观任意行为,语言和“自然”的自然联系由此大大削弱。
(丁)“中国风”的西方文学
18、19世纪见证了西方文学——包括其“古典文学”(古希腊等)——的繁荣昌盛,好比诗云:
【春暖花开看物苏,蓓蕾嫩芽满枝株。
待到微风吹杨柳,万紫千红普天舒。】
实际上,如此西方文学盛况是“汉字表意”所发生的“爆炸性效应”,亦为中国文学之“南橘北枳”所造成的满园春色、满天星斗。而“中国风”则贯穿始终、贯朽粟陈:它先后是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和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主流,而在两者之间(19世纪)则为潜流,说明如下:
第一,18世纪“中国风”之浪漫主义伪造了奠基西方文学的“五朵金花”,即经典版《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以及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后三者比较直接取材于中国。
第二,在18世纪后期,中国风从“显学”变为“隐学”,而其衍生物(哥特等)“喧宾夺主、宣化承流”。在19世纪,潜在的“中国风”汇聚支流和驱动时潮;它们主要是汉学及东方学,但最大而显著的支流则是从中国获取“神秘智慧”的斯威登堡主义。后者与隐身的“中国风”里应外合,而重振浪漫主义和激发超验主义(主要在美国),并且助长了伪哥特、伪但丁、伪史诗和伪希腊(希腊神话)。
第三,20世纪初的“中国风”之现代主义:埃兹拉·庞德和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等人号召欧美文学家亲切体悟汉字,把这个独特的表意文字当做灵感与知识的宝藏,因为汉字是“完美的诗的媒介”(perfect medium for poetry)。他们的这一创举“在西方诗歌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启迪了众多的欧洲、北美和拉美的诗人。
帕特里夏·劳伦斯写道:
【在 埃兹拉·庞德和其他美国诗人构建这种中式新诗之前很久,美国诗歌中的意象主义已与中国诗词传统接上亲缘……。英国现代主义受到中国文学的这种品质的影响。…… 费诺罗萨、翟理斯(Herbert Giles)和 阿瑟·韦利(ArthurWaley)“翻译”中国诗词,主要是唐代的;它使现代主义的想象具体化,亦为现代主义的磨坊准备了精神谷物。…… 庞德越来越成为一个“东方主义者”,他把自己的诗歌研究融入汉字和中国历史之中;从而最重要的发展了文学中的“表意方法”(ideogram method),它奠定了新诗的基础。】
拉斯洛·戈芬(Laszlo K. Géfin)认同:
【庞德编辑和出版的 费诺罗萨遗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使这种表意文字为“现代主义的核心方法和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借喻唐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大家只看到西方文学的“万条垂柳、百花盛开”,而不知道它的种子和根脉则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在西方的土地上长成“碧玉高树、奇妙园林”而已。那裁剪景致的“二月春风”不就是“中国风”吗!西方文学的繁荣只是中西之“因缘、因果”之短暂机遇,故曰:
【“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1913年的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新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艾伦·厄普沃德(A1len Upward)在《神圣的奥秘》一书中写道“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本身构成了最伟大与最古老的人类社会。远从特洛伊尚未建立之前的悠久年代开始,人类的近三分之一人口就已经在它的庇护下生活在相对的文明与幸福之中”。
1913年10月,在厄普沃德的影响下,埃兹拉·庞德开始阅读法文版的孔孟著作,对儒家思想统领下的中国的历史、哲学与诗歌的推崇备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感叹:
【“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取代了希腊。”】
1912年底,庞德结识了女诗人玛丽·麦克尼尔·费诺罗萨——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遗孀,最终获得了其夫的中日文学研究遗稿。庞德如获至宝,惊异于汉字作为诗歌语言的伟大创举,他让中文开始作为诗性语言进入了西方美学视域。“东方似乎正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庞德在写给妻子多萝西的信中写道。
庞德就曾根据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译作创作了一些有中国古诗之风的短诗。希尔达·杜利特尔(H.D.,意象派诗人)曾透露说:
【“庞德正在翻译中国古诗,其中有些相当优美。”】
费诺罗萨的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对庞德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氏“表意文字法”建立在汉字在字源上几乎都是象形文字这种认定基础上,它们所呈现的世界比任何画家描绘的都更逼真,比任何作家书写的更生动。他认为这种象形表意文字当是“世界的理想语言”。
“‘表意文字法’是现代主义的真正原则,”庞德写道,“因为它弃逻辑思辨而青睐精神的内在关联。”这一原则成为庞德在他的中年时期——1940年代至50年代,潜心研究的重点。
在庞德看来,中国古诗对自然景色与个人观察的直观呈现是不折不扣的意象主义,远比费氏笔记中的日本部分更有吸引力“中国是根本性的,日本不是,”他在给纽约的律师兼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奎因的信中这样写道。
1914年,庞德从费诺罗萨遗稿中一百五十多首汉诗整理翻译出十九首,包括《诗经》、陶潜、卢照邻、王维诗各一首、古乐府两首、李白诗十二首,结为《华夏集》于1915年4月由出版商艾尔肯?马修斯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盛赞庞德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但事实上,除了李白《长干行》以外,《华夏集》与其说是翻译,毋宁说是改写。即,庞德改变了传统的直译方式,而采用改写式译法。
四、若非汉语(汉字)则西方无法突破“文字瓶颈”
较之自然物种,人秉赋两个本能:
第一本能(所有生物皆有)——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生存竞争;
第二本能(智能生物独有)——剖析大千,索取万物,反克自然,解放本能(指第一本能)。
第二本能还可概括为: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
所有的技术与知识(包括数学、几何等以及相关的学问)都来自“第二本能”。但它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建设性)与负能量(破坏性);如果处理不好则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在世界联通、海洋时代之前,“双刃剑”对内(本土环境、乡土生态),几乎不能开发“第二本能”(获得技术与知识),否则乃自毁家园、自取灭亡;之后是“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唯有“地缘优势”的国家可以绽放“第二本能”,而其余世界及地球生态则都深受其害。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地理与生态皆是有限的,而且地缘优势也会转移)。
古人如何开发“第二本能”,从而原创技术与知识?
那时,占绝对优势的大自然把人类分散、分隔,而使各个族群皆囿于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稍微“妄动”就会否定其生存,所以古人几乎不能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唯有一种情形乃例外,即在适合的地理环境之中(自然对人是“适度挑战”),在这里,人首先发明“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有序运动、可持续性),运用它来监护与调节之,这才可以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
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能够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与此相反,其余人类——尤其是西方——还必须依靠“神的权威”禁锢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以免自我毁灭。
再问:古人是如何蕴藏、积累、传播和表达知识的吗?
这就需要文字,而且必须是“表意文字”,不能是别的。象形文字只是文字的雏形,而对于知识来说,它则是缺陷;因为象形文字所能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维。用象形文字匹配“文明”(古埃及)只能说明两者都是假的。
至于表音文字(字母文字),即使有(实际上开始于15世纪左右),也只是发音符号;其所含的信息仅仅是个别性、本能性、狭隘性和排他性的,而与人类的“共同认知”(知识)则毫无关系。
对照一下:就其服务于感知主体而言,表音文字是“第一本能”(情欲、物欲),表意文字是“第二本能”(知性、知识);后者并且涵容两种本能而超越之,可以传导形而上的心灵意识。
第一本能(感官、耳识、杂识)→表音文字(近代初)→狭小时空
第二本能(潜能、意识、知识)→表意文字(古汉语)→超越时空
自从17世纪末以来,西方诸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从而胜任于记载和传达知识。于是,西方便宣称(我们也都信以为真):它的表音文字如何优越(原本具有“合理表意”),而且是“古已有之”,所以谱写出“希腊智慧”(文学、科学和哲学等)。
西方不可能原创或原生知性与知识、文字与文明。即使到近现代,由于天时地利的转移,使之拥有地缘优势,双刃剑(负能量)向外,从而能够绽放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但如果仅凭己力,不靠东方助缘,那么,西方独自发展,一两千年也达不到宋朝的水平。
再者,即便是西方依靠地缘优势,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资讯,并且使全球资源财源向己方滚滚倾注,从而能够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但如果它不突破“文字瓶颈”,即设法使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那么,西方则必是一事无成、百业不兴。
版权声明:文章版权属于作者本人。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
上一篇:从美国的贵族教育看教育分层:你的命运一开始就已经被注定
下一篇: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汉字密码”
相关推荐
- 日本去年出生率创123年以来新低,每年关闭超400所学校
- 教师≠编制 越来越多中小学教师岗和编制脱钩
- 伊顿公学培养英国首相的历史
- 教育部:职业教育决不是单纯的就业教育
- 农村兴起择校热陪读热 80后90后父母拒绝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3天获利近千万?隐秘而疯狂的小学奥数竞赛“生意”背后
- 哈佛幸福课的8个幸福秘诀
- 幸福的配方
- 魏书生用“老办法”做出新成绩:从“甩手”校长到“放手”局
- 每年就诊量上升10%-15% 青春期孩子是强迫症发病高峰
- 疫情之下,请这样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 新政重塑教育格局——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1
- 大学教育如何避免“白开水化”
- 开学在即 北京新学年教育领域有这些变化
- 西方三位哲人眼中的汉字观